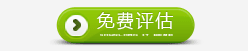瑞典為什么有那么多創業企業?
這是一個高消費、高稅收的國家,勞工享有悠長的假期和豐厚的社會福利。主流經濟學認為,像瑞典這樣的國家不利于企業成長,因為高稅收會降低企業家的盈利預期,進而挫傷他們的創業積極性。而研究也表明,一個國家的人均政府支出越大,這個國家創業企業的比例就越低。
但瑞典是個例外。這個人口僅千萬(全球排第89位)的國家盛產創新企業,音樂流媒體平臺 Spotify、在線支付公司Klarna、游戲公司King等世界級企業都在瑞典創立。斯德哥爾摩“科技大牛”的密度(市值超過十億美元的科技公司的數量/人口)僅次于硅谷。整體而言,瑞典每1000位雇員就對應著20家創業企業,在美國這個數字僅為5。OECD 經濟學家Flavio Calvino 告訴我,“在瑞典,創業企業的存活率高,且發展快”。一項針對18-64歲人群的調查發現,65%的瑞典人認為他們國家的創業機會“好”,在發達國家中,這個比例是最高的,美國僅有47%。
創新創業,對一切追求效率、就業以及活力的經濟體而言,都至關重要。在美國,盡管創業的激情還在,行動卻明顯遲緩了——如今創業企業在美國企業的占比為8%,而在1978年這個比例是15%。在瑞典,情況恰好相反。1990年代以來,瑞典加快了創新創業的步伐,近兩年經濟增速更達到4%和3%——較之增長低迷的美國,可謂“大躍進”;也比其他歐洲國家也快得多。那么,瑞典到底做對了什么呢?
可以從幾個層面來探討這個問題,不過都繞不過過去30年的瑞典變革。1990年代以來,瑞典放松管制,釋放出創業企業與既有大企業競爭的空間。經濟學家熊彼得認為,當“創造性的毀滅”發生時(亦即創新力量取代舊產業時),經濟才會繁榮。但摧枯拉朽并不容易,曾經瑞典也是個嚴格監管經濟的國家,公共事業單位壟斷了市場。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金融危機的爆發。
危機爆發后,瑞典增速下沉,失業率飆升,政府為避免貨幣崩盤,甚至將利息上調至500%。改革勢在必行。瑞典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Lars Persson告訴我,為提振經濟,瑞典政府著手給電力、電信、鐵路、民航、出租車等行業松綁。限制取消后,各行業的費用降下來,吸引了更多消費;部分公共服務,如養老和基礎教育,則外包給私營機構。1993年,新“競爭法”出臺,明確限制大并購及反競爭行為。“我們的經驗是,只要市場不形成壟斷,新的企業就會進來”,瑞典皇家技術學院的Pontus Braunerhjelm教授總結道。
另一條經驗就是削減公司稅,提振企業家精神。關于這一做法,坊間頗有爭議。具體到瑞典,效果確是不錯。1991年,瑞典將公司所得稅從52%下調至30%(如今這個數字只有22%,遠遠低于美國的39%)。而在此之前,瑞典稅法明顯傾向大公司,而非創業者:創業者除了公司所得稅,還要交個人所得稅;大公司卻有種種途徑避開雙重征稅。
稅率改革創造了公平競爭的環境。而 “1991年以前”,Persson在去年的一篇論文中寫道,“瑞典稅制偏向機構持股的大公司,缺乏資金的小型創業企業很難存活”。進入2000年代,瑞典把富人稅和遺產稅一并取消了,讓“掙大錢”成為可能。這樣一來,人們掙錢的積極性就高了,掙到了錢又會再投資,錢生錢。Braunerhjelm教授認為,“人們手里的錢多了,天使投資人就會出現”。在今天的瑞典,創業者享有很大的稅收優惠,比如他們的大半收入被認作是“資本利得”,相應的稅率要低得多。
減稅不一定管用,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Tino Sanandaji承認,還可能加劇經濟不平等。但瑞典的經驗表明,有針對性的減稅是可能為經濟注入活力的。瑞典素有“高稅收”之名,1991年稅改之后減了不少,現如今公司稅已經低于其他發達國家。稅改前,瑞典最高邊際稅率為85%,改革后降至57%。現在的瑞典稅制相對“扁平”,個人稅負差別不大,也就是說不僅有錢人要多繳稅,普通中產的所得稅也相當可觀。不過,多數瑞典人對此沒意見,因為作為對“高稅收”的回報,他們享有“高福利”,看病、上學都不花錢。
1990年代前,瑞典經濟幾乎沒有外來競爭。保護主義的立法禁止外國人大量持有瑞典公司的股份,只有不到5%的私企勞工受雇于外國企業。此后,瑞典改革開放,引入外來競爭。一則外資可以收購成熟的創業企業,如2014年微軟以25億美元收購瑞典游戲公司Mojang,大大激發了瑞典人的創業熱情;二則外企進入瑞典市場,迫使經營不善的瑞典企業退出競爭,為創新企業的崛起騰出了空間。1989年外資僅持有瑞典公司7%的股份,1999年這比例已上升至40%。
1990年代的瑞典改革適逢互聯網經濟的興起。人們在創業的同時,第一次親密接觸互聯網。凡是給所有員工(不論是管理層,還是保潔員)配置家庭電腦的公司,瑞典政府都給它稅收優惠。很快,電腦就普及開來,“40歲以下的瑞典人都是玩電腦長大的”,倫敦風投公司Northzone的合伙人PJ Pärson告訴我,“1990年代就人人在線了”。此外,瑞典也是最早大舉投資,提高互聯網速度的國家。今天瑞典的電腦普及率和美國差不多,但網速仍比后者快得多(平均22.5MB/秒,美國只有18.7MB/秒)。
33歲的Birk Nilson,是這一代創業者的縮影。在孩提時代,他就有電腦,11歲開始編程,16歲到科技公司打工。19歲的時候,Nilson遇到他的合作伙伴,一起成立了電子商務公司Tictail。
和瑞典許多創業企業一樣,Tictail從一開始就是“全球的”,用Nilson的話說, “我們本能地會考慮出口”。和美國不同,瑞典是個小國家,市場有限,企業要做大就得有全球格局——把產品賣到海外,同時承受海外競爭的壓力,優勝劣汰,適者生存。Tictail已獲得3200萬美元的融資,不久前把總部也搬到了紐約,還在下東區開了個店。
創業帶來就業。據經合組織(OECD)統計,瑞典每100個就業崗位里,有5個是新崗位;而在美國,這個數字是2。OECD 經濟學家Calvino告訴我,“去看就業機會凈增數據的話,你會發現瑞典總是名列前茅”。此外,瑞典創業企業的“3年存活率”也是最高的——74%的瑞典創業企業可以活過3年。
自然,漂亮的創業紀錄與“瑞典模式”是分不開的。比如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,讓創業者敢于放手一搏。在瑞典,高等教育是免費的,學生還能申請生活貸款,人人都上得起大學。看病也不要錢,生孩子的話,還有可觀的生育補貼。換句話說,你無需為生老病死教育而擔憂,哪怕創業失敗,也不會失去一切。
“我認為要成為創新國家,你首先得給人們足夠的安全感,”瑞典企業與創新部部長Mikael Damberg總結道,“這樣他們才敢去做”。對此Birk Nilson深有體會,他知道就算他的公司辦不下去了,他的醫療保險也不會少。“就算失敗,就算破產,你也還有瑞典和它周全的社會保障”,Nilson對我說,“在瑞典創業,不像在美國這么嚇人”。
此外,還有社會文化層面的因素。比如Nilson和伙伴們經常有機會跟Spotify或Klarna的創辦人一起工作,討教創業經驗,創業者之間的這種交流對彼此都是促進。烏特勒支大學的Erik Stam教授告訴我,瑞典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度很高,這讓他們合作起來更順暢。比如他們往往一拍即合,而不會在合同上錙銖必較。又比如上級信任下級,就容許他們彈性地工作,而彈性產生創意。
相應地,瑞典的“內部創業”(intrapreneurship)也很活躍。企業內部設置“孵化器”,進行“非常規”開發和創新。比如愛立信公司有個部門叫做“愛立信車庫”,從可穿戴技術到助老工具,各種五花八門的技術都研究。斯德哥爾摩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表明,過去三年里,瑞典有28%的企業員工參與了內部創業項目,而在美國,這個數字僅為11.7%。